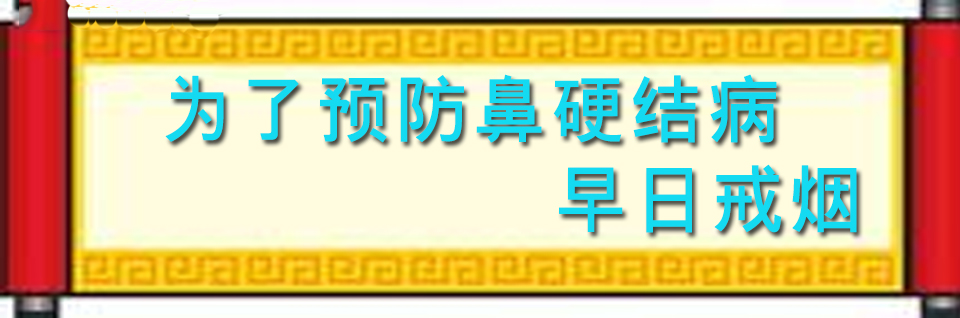雪儿
1那是一条从我生命里匆匆而过的黑色野狗,它正张大嘴巴,露出白而尖的獠牙,仰天长啸。四周无人,一片寂静中,我走向它,它快速跑过来,将两只锋利的前爪搭在我身上,伸出粉色的舌头舔我的脸,我弯下腰,用全部手掌抚它的头,温柔有力,它黑色透明的眼眸闭上了。我蹲坐下来,它也坐了下来,把头靠在我身上。摸到它脖子上的硬结,我知道那个伤口;我又反复在它的后腿上确认,没有伤口,我开心极了:原来没伤到腿部。药膏呢,一直收在枕头底下的药膏,为什么怎么找都找不到。我急得大哭,泪水浸湿了枕头。一条灰褐色的蛇出现在床底,我浑身无力,动弹不了,只身变成一把剪刀,将蛇的身子剪成两段,一瞬间,蛇身断裂的部分又长出了一个头,我继续剪,满屋子的蛇吐着猩红的信子向我蠕动,从四个床角往上爬。我把头蒙在被子里,并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蛇争前恐后地钻进了被子。醒来时,紧咬牙关的我大汗淋漓。2两堵红里透黑的窑砖,爸爸说这批砖烧老了些,所以不漂亮,刚刚好的砖是亮红色的,像晨曦的颜色,但这批正卡在砖刚韧的火候,最好用,再过一点,就老了,像人老了,骨头承受不住压力。我躺在两垛砖的中间,看着满天的云,形态各异,来了又去,没有重样;这儿真是个巧地方,正山脚下的一块坪地,热烘烘的风儿经过树林,全都降了温,凉凉爽爽地吹过身体。爸爸说地上有毒蜈蚣,妈妈说泥土的湿气扯到人身上老了会骨头疼,但我总是趁他们不注意,偷偷溜到这儿,尝试着给云朵取名字编故事,听着山上各种鸟儿叫,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今天,是中秋,家里热闹非凡,爸爸忙着陪酒,妈妈急着做饭,好了,有了一下午没人管的时间,我从从容容地夹着一本书,躺在了这个宝地,看会儿书或瞟一眼云。一阵可怕的"窸窸窣窣",一条灰褐色的蛇吐着信子慢慢地游了过来,脖子上有一个字母V,砖垛后面的大公鸡,将头伸得很长,脖子上的毛一圈圈立起来,摆好了决斗的架势,但它没见过这么大的虫子,或是家族里有被蛇咬的经历,犹犹豫豫地不敢下嘴。蛇的信子马上就到了我赤着的双脚,我吓得动弹不了,雪儿窜了过来,咬住了蛇,蛇被惊吓,反口噬住了狗的脖子,狗含着蛇往后山跑了,脖子一路往下滴血,我赤脚跟在后面,但它很快消失在大山里,走了一条我找不到的路。我坐在山口,就是它第一次等我的地方,不一会儿,它出现了,我唤它,它像没听见,头没回,只是无力地歪向一边,后面的右腿有些瘸,不知道是不是也被咬伤了,消失在无边的树林里。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它。3那是我第一次和狗狗心灵相通,它骨架很大,没人的时候总是眼神坚定,步履匆匆,好像要急着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但见人就眼神躲闪马上掉头,换个方向更快速地走,好像又有了新目的地。偶有人拦住它的去路,想逗它玩或捉弄它一回,它通通当做没看见,马上转路。小学三年级的冬天,那年特别冷,一场接一场的下大雪,被妈妈用围巾裹得严严实实的我慢吞吞蹭在去学校的路上。远远地,简易公路上围了一圈人,我赶紧冲过去看热闹:一辆拖拉机停在路边,"突突突"地没熄火,两个男人使劲拖着一个绿色大网兜,网兜缓慢地移动,与地上黄色的冰雪渣子擦出"哧哧"的声音,我低头一看,是它。"捕杀流浪犬,保全村安宁。"拖拉机身上挂着横幅,村长笑着给拖狗的两人递烟道谢:"对对对,这条狗不是村里家养的。"它趴在网兜里,周边满是人却无法如平日转身,只是用爪子牢牢抠住地面的积雪对抗拖力。第一次,它安静地用眼睛一个一个扫视身边的人,眼睛里喷涌而出的祈求和渴望,如一束耀眼的阳光,刺亮了我的心。昨天课间的时候,在一群同学的质问中,我也用这样的眼神盯着同桌,想让她为我作证:我的作文不是抄袭的。同桌移开了凳子,马上就要站起身,却又转念在大家的注视中坐得更稳当了,低下头,避开我的眼睛。我挤上前去,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是我家的狗。然后连着网兜一把抱起了它,踉踉跄跄往后山跑,把大家的质疑声丢在漫天飞舞的雪花里。终于安全了,我和它一起摔滚在后山坡上,它浑身沾满雪花,抬起头看着我,那是一双黑葡萄一般的眼,往里看去,仿佛融着泪光。“雪儿,过来,雪儿是你的名字,这座山就是你的家。”我摸着它的额头,对它说:“现在我要去上学了,放学后来找你。”然后,我跑向去学校的路,它没来追我。后来,不论我去哪儿,它都任我走从来不追,只是在唤它的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它都像一阵风,不知道从哪个角落窜到我的跟前。后山是我们最喜欢呆的地方,有时候我给它带了吃的,更多的时候是我躺在山坡上看天上的云,它在旁边忙得不亦乐乎:衔来一堆松球;用爪子逗窝里的蚂蚁或者满山的疯跑,隔一会儿在我身上蹭蹭。常常,它也会安静地坐在我的身旁,一起眺望深山外的那条简易公路,想象路的尽头是不是还是连绵的大山。在这儿,我们自信、友好而调皮。4日子云一样的飘来,又水一般的流开,马上过了夏天,四年级的第一个学期,转学来的新同桌是有着一头乌黑长发的女孩,她温和大方,同我一样喜欢看书,我们形影不离。“我有了第一个好朋友,有好朋友的感觉真奇妙呀!”第一天放学,正向雪儿汇报时,一阵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我们赶紧趴下,把身子藏在满坡的黄色野花里。我们默契地不发出声音,以免大人呵斥,他们看到它最常说的是:滚,畜生,怎么又是你!它听到了后,就像一个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是又没办法不再做的孩子,低垂着头,夹着尾巴,悄无声息地转头消失了。那个学期,班上有女同学头发上开始长虱子,防范于未然,妈妈给我剪了短发,同桌上课的时候总是用双手紧紧地护住头顶,好像这样就能不染上虱子。每天放学,妈妈都会拨开我的头发,检查一番,头上无恙,一个晚上,我的手背和肚皮却开始奇痒,长满了红色的疹子,直到妈妈打着手电筒在我身上抓到了红黑色的跳蚤。她大声叫:跳蚤,让你不要和那条狗混在一起,这是狗身上的跳蚤!第二天,妈妈用一个大木桶将被子和床单装到山后的池塘洗了;把垫床的干稻草用火烧光,床板被一块块搬到阳光下暴晒,最后在四个床脚喷了厚厚一层杀虫剂。晚上,果然不痒了,疹子也消了大半。但隔天,我依旧在妈妈的恐吓下用破碗装着晚餐走向了后山并保证不碰雪儿。“为什么不让你养狗,现在知道原因了吧?你看......”妈妈的唠叨声一路飘到山坡。雪儿一如往日,健壮的身体跟不上它想要的速度,一个罩头翻到了我的跟前,又马上挺身而起,两个脚搭到我身上,我把手摊开,藏在里面的是一块油津津的肥肉,它一把卷入嘴里,又用舌头舔干净手心里的油,才低头吃碗里的饭。吃过饭,我将它带到红色夕阳能照到的山顶,用手理开它黑得发亮的毛,果然,毛丛里跳出一只只芝麻大小的跳蚤,我掏出杀虫剂将它的周身喷遍,杀虫剂的味道很难闻,我们都被呛得打了很多喷嚏,但它一动不动,闭着眼睛。事毕,我又带它去了爷爷坟头边上的沙堆里,带它滚了会儿沙子,希望滚干净她身上的跳蚤。当天晚上,我痒得在床上翻滚不敢唤妈妈,第二天,一进教室,就发现又有几个女同学剪了短发,我的同桌眼睛通红的抱怨:她晚上不敢睡着怕妈妈剪头发,又说妈妈说只要在她身上看到一只头虱就要给她剪光头。我们惯例拨开对方的头发检查。“跳起来的,一只可以跳的是什么?”她大声尖叫,我满脸通红低头不语。“你知道自己长了?”同桌急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用双手狠狠地捂住自己的脑袋:“怎么办,怎么办,我的头发,我不想剪短发。”“这不是,这不是头发上长的......”我语无伦次。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走过来,拨开我的头发,开始讨论我脖子上密密麻麻的疹子,说我身上长了变异的虱子,会跳。同桌一言不发,把书包搬到了教室最后面的空位上。早自习开始了,大家都拿出了语文书大声朗读。我在读书声里重回了独来独往的小学时光。放学后,我捏着全部的零花钱来到供销社的药柜,想买治跳蚤的药膏。"没有药膏,衣服被子洗干净暴晒,艾叶煮水泡澡可以止痒。"工作人员说。"什么?狗?把狗赶到外面,不要让进屋。"药店人被怯怯的我弄得不耐烦。"狗是畜生,和人混在一起,那人身上一直断不了,到时你全身的皮肤都会被咬烂。"回到家,我主动将雪儿的饭碗扔到了后山茂密的树林里,妈妈一边骂一边重新帮我换铺盖:“狗身上的跳蚤清不干净的,它浑身是毛,怎么弄得干净。”每天在教室门口守着,检查我脖颈和手上的红疹成了几个同学的恶作剧和我的噩梦。我不再去后山的第三天,第一次,在我上学的路上,雪儿从后面追了过来,它好像瘦了很多,又好像没瘦,如之前一样,它迫不及待地将爪子往我身上罩,它的速度很快,但落爪子时却很轻,以至我轻轻一推,它就倒在了路边的水田里。我记得它马上利落地爬起来,又摇头晃尾地跑向我,我用手挡着,往后退,害怕地大声说:滚,畜生!它停了下来,困惑地用黑葡萄一般的眼睛盯着我,往内看,里面好像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洞,然后摆了摆头,转身,换了一条路,消失了。不到一周,我身上的疹子就消退了,同桌最后还是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我不再偷偷摸摸地把肉藏在手心,也不必步步为营地讨时间去后山找雪儿。雪儿就这样,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5这个中秋节的下午,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它。那天下午,刮着漫山遍野的冷风,我光着脚寻遍山里的每个角落,没有雪儿,却第一次看到了它安在松树下的家,窝旁边的矮草凌乱不堪,沾着零散的血,一定是雪儿刚刚在上面滚过,它是疼痛难忍还是只想滚干净身上的血?窝却收拾得井井有条,垫着我抱它回来时绿色的网兜,靠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我们玩耍时丢掷的石子、我撕碎的旧书皮和几个铅笔头、已经空了的杀虫剂瓶子。窝的最中间,放着它的饭碗,我扔在后山的碗。因为有一个缺口妈妈说不要了的那个碗,无数次我猫着腰避过大人,端着满碗饭菜走向后山的碗,被它衔到了家里,碗面干干净净,衬出天上大而圆的月亮。很快,天黑了,妈妈唤我回去吃饭的声音。我在山头坐了一会儿,就是在这里,那个落雪的早晨,我气喘吁吁地告诉它:雪儿,过来,雪儿是你的名字,这座山就是你的家。然后它就住了过来。
它从不来家里找我,但一定知道我的家在哪儿,但我,我从没想过它晚上睡哪儿,也没去过它的家。它怨过我吗?它应该要怪我的。
妈妈唤我的声音越来越急,我赤脚跑回家,一路踩在雪儿刚滴的鲜血上。几天后,吃饭时,我若无其事地和妈妈说起几天没见到那只黑狗了,妈妈说,那本就是一条野狗,也许去了其他村庄。我又装作云淡风轻的样子,问爸爸:一种灰褐色的蛇,头顶有V型标志,有毒吗?爸爸说,有剧毒。三个月后,姨妈家的孩子出生了,双眼亮如黑葡萄,九岁的我在一众大人中脱口而出:“妹妹的小名叫雪儿吧!”"叫什么雪啊霜的,太阳一出来就消散了,叫石头。"姨父掉了脸,像是自我安慰地又加了一句:"童言无忌,说破了就没事了,平安百岁平安百岁。"
四年后,我从无数次与雪儿一起眺望的简易公路离家,外出求学。后来,我忘记了雪儿,却习惯买回各种根治宠物身上跳蚤的药膏,存在家里,过期了再买回来新的。色温杨梦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