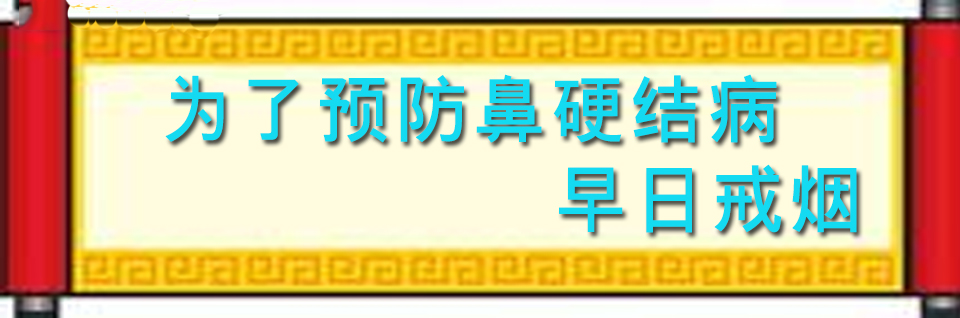当前位置:鼻硬结病 > 疾病预防 > 艾滋病女为了救他,我沦为玩物 >
艾滋病女为了救他,我沦为玩物
作者
云夕何兮
01冷晴二十八生日那天,收到了一个特殊的礼盒。
这个礼盒包装精美绝伦,彩色的织带细细密密的裹缠出梦幻的彩色。所谓姐妹们一口一个,哇塞,这是谁送的?
啧啧啧,真是出手不凡的主啊!
彩儿上前挽住冷晴,贴的假睫毛因为她过度的表情歪了,露出眸子底下遮掩的不甘。
她们同为姐妹,以有色的生活,做一场人生的交易。凭什么都是脱光躺男人身底下,冷晴却可以比她挣得多几倍?
冷晴不着痕迹的推开了彩儿的手,洋溢的笑有些安然,一只手不紧不慢敲打着礼盒,“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件事没告诉姐妹们。”
“我辞职不干了。”
几个女人疑惑的互相看看,问:“晴姐可是有了好去处?”
有男人长期包养,是从事这行的女人所谓的一个好去处。
冷晴笑笑,拔掉了彩带的一根,“是彻底不干这行了。”
礼盒的彩带细细密密的缠绕,一圈又一圈,相互拉扯着,纠缠着。
冷晴想不出送这礼物的人,到底是谁。是谁会把礼物缠绕成茧。
彩儿自嘲的笑,“晴姐这是脱离苦海了?”
冷晴停了手上的动作,坐在一旁的软凳上,失落空荡一笑,“算是吧。”
“他,上个月走了。”
冷晴口中的他,是她的丈夫,王串子。
02倒回去几年的时候,王串子也是这片有些名气的人。
他有一把好力气,会点身手,热心肠,总帮着街上的老人,提个重物,送个物件。
人不如其名,他只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冷晴和他是一起从大山里走出,到城市打工的农村人。
在这座城市里,一对新婚夫妇,一片狼藉的钢筋混凝土下,几间建筑工的简易板房内,拥挤的过着普通的日子。
串子说,晴晴,等我们攒够了盖房子的钱,就回去老家,修一栋小洋楼。
整一排简易的猪圈,养肥猪卖肉挣钱。
再也不用坐在地上吃饭,蹲在高空拉屎。
干过建筑工的都知道,修高层的时候,一口气踩着简易钢梯,直直爬上几十层楼做工。拉屎这种事,不过就是找个隐秘的地解决,不论男女。
穷人,没有什么讲究。冷晴从来不在意这些,她也是唯一一个愿意上下爬几十层楼,去简易工棚的厕所拉屎的人。
她读过些书,长得也清秀可人,成绩一直不错。可家里兄弟姐妹太多,义务教育结束。
她的读书生涯也结束了。
在家帮着父母干了两年农活,出落的健康苗条。媒人提亲,不过是串子的爹娘将攒了多年的棺材本,换回了这个不错的媳妇。
说来也巧,虽是带着些老一辈的说媒成婚,却也还算是段好姻缘。
串子善良本分,健硕又有把子力气,外表也仪表堂堂,花季的冷晴一眼便上了心。想来应该是缘,冷晴想,自己的命,也不算太坏。
上帝赐一场良缘,却不肯赐一场圆满。
03这句话,是串子出事后,冷晴最后划在工地的二十八层天台上的水泥墙面上的。
串子是在六月的一个烈阳天,从工地边上推开一个钻入工地玩耍的孩子,受了孩子头顶飞速砸下的一袋水泥。
三十八层,一袋水泥,串子的头变了形。
医生抢救了两天两夜,推出了白布包裹的串子。
警察,工人,领导,媒体记者,所有人都涌上前,包围着那张绿色的推床。冷晴挤在一旁,撕心裂肺的哭。
哭串子,也哭自己。
医生说:“患者经过全力抢救,已经暂时脱离生命危险。”
冷晴喜极而泣,她就知道,她的串子,不会那么狠心。狠心丢下她一人,在这漆黑的世界,爬走。
医院守了半个月,寸步不离的守着她的丈夫,串子。
半个月,他没有睁开眼,也没有同这个苦苦守候,以泪洗面的女人,说一句话,看她一眼。
医生说:“他……可能是暂时的无法苏醒。”
冷晴哭着问:“那他什么时候能醒?”
医生回:“这个……说不好……有可能很快,有可能一辈子。”
“简单来说,他现在的状态就是植物人。”
冷晴的泪僵在眼眶里,流不出,忍不回。久久滚烫烧灼那双清水明亮的眼。
那一段时间的报纸,新闻,电视,都是一位农民工奋不顾身牺牲自己救了一个孩子的报道。
冷晴恨极了,疯狂的撕碎好心人寄来的钱和信。医院的电视。
有人说,她疯了。
04冷晴知道,她只是太讨厌听见别人叫她的串子,她的丈夫,英雄。
这座城市的英雄,是串子用命从别人口中换来的。
冷晴什么也不要。她不要英雄,不要锦旗,不要钱。她只要她的串子,活蹦乱跳的在她的身边,喊她,媳妇,等我攒够钱,就回家养猪卖肉挣大钱!
午夜梦回的醒来,她分不清现实和梦境。在医院的走廊大声的笑,跟旁人说,我老公上夜班挣钱呢!
有人安慰她,迎合她,不忍心看她。
她却哭了,指着串子的病房喊:“我男人就躺在里面,半死不活!”
“可我,半点也救不了他啊!……”
她的哭声,撕心裂肺的撕碎黑夜,打破昏黄灯光的温暖。七月的黑雪,纷纷扰扰的落进她的生命。结成厚厚的蜘蛛网,围困,缠绕,窒息。
一年后,这座城市里已经有了无数新的人,新的新闻。串子的事迹只在发黄破损的破烂废纸上可见。
没有人去看一张旧报纸,也没有人记得一个植物人。
夜雨声烦,落尽人间冷暖,淋透冷晴,走进那家金碧辉煌的天上人间。
她脱了衣服,露出姣好丰盈的身体,有人笑,说她好货色。有人摸,说她好滋润。
05有人问,做这一行有什么故事?却没有看一眼她干瘪枯黄的魂,她僵死腐烂的心。
她说,我卖身治我男人。
众人先笑,继续逗乐子,讲笑话,办事。
办完事,提裤子的时候,却又总记得问冷晴一句,“你说的是真的?”
冷晴扣上最后一颗扣子,点点头。男人哀叹一声,同情道:“太可怜了。”
红票子也甘愿出得多一些,冷晴医院的玻璃窗口,看那个穿着洁白护士服,面容干净的护士用一双娇嫩的手收走它。
有人说,钱是这个世界最脏的。
冷晴到现在才知道,这话是错的。
没有人会嫌钱脏。冷晴不会,护士不会,医生不会,你也不会。
就这样,冷晴靠着这行,医院躺着的串子,在呼吸机和管子上活了八年。
八年后的一个晚上,她正在陪酒,胃里汹涌。一个电话解脱了她,是医院的号码。冷晴放下酒杯,赔笑,“不好意思,我先去接个电话。”
一熟客打趣,“玩得起兴,你就要跑。大半夜的,谁给你打电话?”
冷晴依然赔着笑,“医院的,不能不接啊。”
“医院?哦……差点忘了,你是有故事的!”
“去吧……去吧……”
冷晴低着头走,身后的一个客人依然在说着:“你说冷晴那植物人老公,会不会是要诈尸了?”
另一个哈哈大笑,回:“要是诈尸,怕冷晴也心甘情愿和鬼睡啊!她多情深义重啊!”
灯红酒绿,人心凉薄,冷晴失笑,哪有什么情深义重啊。
不过是,一句不舍罢了。
不舍,她的串子,就那么死透了。
医院电话接通,主治医生熟悉的声音,有些停顿。
06冷晴问:“医生,串子醒了?”
医生更加闪躲,“冷晴,你要……”
“那就是死了是吗?”
话筒里冰凉平淡的声音,透过电线传来。医生一愣,回:“嗯。”
“患者于几分钟前已经确定脑死亡。”
冷晴忽然笑了,淡淡的,解脱的,“谢谢医生。”
电话挂断后,她照常坐回刚才的位置。男人见她回来,开刷道:“冷晴啊,怎么?是不是你老公诈尸了?”
冷晴冷笑一声,松了酒杯,任由它自由落体,砰的一声碎了。冷晴笑着回:“是我那苦命的老公做了鬼。”
“做了鬼。”
冷晴重复一遍,又笑起来,走出了天上人间。走去黑夜里,走在月光下,走在平坦的人行道,走在宽阔孤寂的大马路。
从此,她再也不用挣医药费了。
不用把那些红票子,医院的坟墓。
半个月后的今天,她的生日。这是第一次,告别这座城市。也是最后一次,告别这座城市。
礼盒拆完了缠绕的带子,彩儿退了几步,欲言又止。
礼盒里静静地躺着一件寿衣。
一张精致的卡片上写着:不用说谢谢,欢迎加入艾滋病俱乐部。
署名:曾经的恩客。
围观的女人面面相窥,猛地退远了几步,和冷晴保持了距离。
07死寂一般的沉默,女人们欲出口安慰,却被冷晴接近癫狂的笑吓白了脸。
冷晴说:“真好。”
“可以早一点去找串子了。”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嫌我,嫌我,脏。”
彩儿再也忍不住,跪在地上,泣不成声,煽自己耳光,“冷晴姐,那个礼盒只是个玩笑!”
“是我送的。你千万别想不开啊!”
其他女人恨得牙痒痒,上前拎着彩儿狠狠地打,踢,骂。
冷晴却视若无睹,不急也不气。拿出纸巾擦了口红,湿巾纸抹了妆容。
光着一双脚丫,走进夜雨里。
这是一场,深秋的夜雨,丝丝缕缕,凉意入骨,冲刷着人间,冲刷走生命的痕迹。
也许,明年春天,也不会有人再记得,天上人间,那个有故事的姑娘。
一个有故事的姑娘留。
暖叔说:为什么今天发这篇文章,因为有个新闻“19岁女学生感染艾滋报复社会,传染给至少男性”
这是发生在高校的事情。
真真切切,不是肮脏的黑市,不是乌漆墨黑的小巷,是活泼青春的大学校园。
不知道是疾病造就了魔鬼,还是本身是魔鬼,用别人的不幸去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
洁身自爱,自尊自重,一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END
暖叔嘿,亲爱的们,给入不敷出,日渐消瘦的暖叔,点点底下的小卡片广告吧,这样吃土少年就可以获得奖励三毛钱~比心
暖叔的生活观赞赏
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