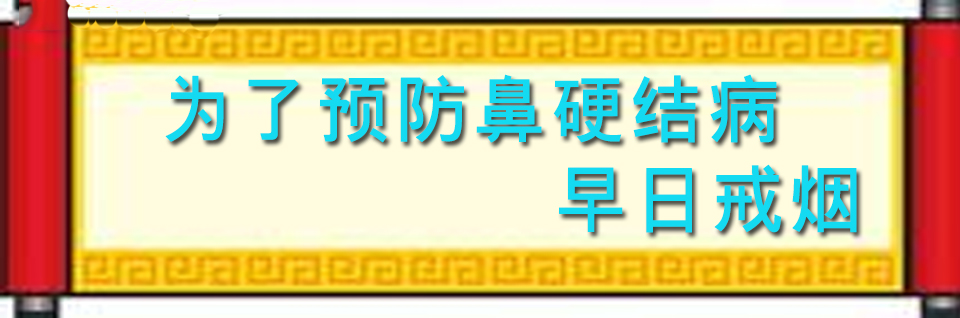当前位置:鼻硬结病 > 病因病理 > 祭毒12海洛因带他们去了一个世界 >
祭毒12海洛因带他们去了一个世界
文|李宗陶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
李宗陶:
那是年初春,我不知怎么有一双有蓝色缎带的鞋,缎带系在脚踝上,可以打个小小的蝴蝶结。我踩着那双鞋子穿过某个劳教所的操场,感觉操场上光头们的视线都集中在那双鞋上,这让我浑身不自在。
那一年,我在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和中英艾滋病项目的帮助下,以调查员的身份接触到某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群体。一年里,我去了四次,每次停留十天到两周,在当地疾控中心陈医生的协助下家访,并且访谈,就有了这本《祭毒》(作品原题)。
那一年春天,我刚刚从美国回来,加入《南方人物周刊》,同时在做一些文史哲学者的访谈,并且产量不低——大概是自己这台写字机闲置了一年,动力十足的缘故。
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实习的三个月里,我接触了那个国家一套应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机制,从政策到治疗,跟我后来看到听到的有很大不同。有点像一个人先去学了古画修复技术,然后被领到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存放古旧的地下室。
这份田野调查完成后似乎只给一两位师长看过,然后就一直待在某个移动硬盘里。将近十年过去,移动硬盘也失了灵,读不出数据。感谢复旦大学附近某个电脑维修店的小伙子把这个文档救活了,只是现在拿出来,有点难为情——没关系,也都是这样写过来的。
《祭毒》(1)
海洛因带他们去了一个世界,然后拐向另一世界
你不能指望太多。每天翻开报纸,社会新闻就是这样例行公事讲着快餐故事。故事比较简单,好与坏、正与邪、是与非,一目了然,虽然也总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我想告诉你这故事后面还有什么――
这天,毛向阳其实像个要去登山的人。他的确戴了一顶蓝色棒球帽,正前方带两道竖杠,这让他看起来像一只昆虫。一件米黄底色的运动衫,胸前有橙色与蓝色的镶拼,将主人的惨白脸色稍微中和。
店门已经关上,警察已将四周包围。毛向阳摊手摊脚坐在商店办公室的折叠椅上,背靠着墙,脚跷在柜台上面,让人看到了他的名牌球鞋与裤腿带拉链的运动裤。他用右手二指轻捏针管,左手二指夹一支烟,间或猛吸一口,喷出一团浓烟直扑经理脸面,他表现得像一个老牌无赖。他看到那个长得很标致的小妹,穿着电信蓝制服的那个,匀称的小腿在丝袜底下瑟瑟发抖,他自己跷在桌面上的脚也在抖,不听使唤地停不下来。
“3万,一分钱都不能少!”这话他已经讲了三遍。经理捣蒜似地点着头,却不见动。
玻璃窗格上突然贴出一张母亲的老脸,眼泪汪汪,嘴唇哆嗦,隔着蒙灰的窗玻璃不知在说什么。总用这些老掉牙的办法,他在心里冷笑一声,别过头去。
荣东,他朋友,也是“艾滋病”,没多久也来了。荣东是当地强人,黑道上听见“荣家两兄弟”的名头都要买账。荣东左边肩膀上刺着一条青龙,右边盘踞一只苍鹰,小臂上还有粗粗拉拉“小芳”两个字,那是女朋友的名字,他自己刺的。
荣东进了经理室,什么也没说,忽然弯下身子替他将松了的鞋带系好。毛向阳很受用,想再点根烟。警察忽然就冲进来了,一根黑色的大棒直直向他头部压来。眼前一黑。
晚报报道中没有提及,“这位男子”当时是被电警棍制服的,“里三层外三层,消防大队、防暴大队、辑毒支队、公安局治安大队都来了。娃儿开始硬气得很呢,结果两棍子就被电倒了,像只死鸡一样被两个警察抬上警车开走喽。”这是围观者的描述。
醒来后,毛向阳已躺在派出所的长凳上。他听见值班警察正对治安大队的人说:“哦哟,你们又给我拉了个死人来。”例行公事:尿检。试纸上两道红线,表明受检人三天内曾经吸过毒。其实不用化验也知道,他的面孔辑毒警太熟了,熟得好像自家兄弟。照理,毛向阳该送戒毒所,但他的CD4(注1)低于,是处于发病期的艾滋病人。按照规定,戒毒所、劳教所都不接收处于发病期的艾滋病人。警察也懒得跟他废话,直接放他回家。
当天晚上,“胖妹”把儿子托付给朋友的母亲,回家旋开农药瓶,大口吞咽气味刺鼻的液体。一根滚烫的导火索,沿着喉咙、食道爬向胃部,迅速在体内燃烧。这是她在一周内的第三次自杀。她其实不想死,第一次,她喝了一小口,肚里觉得烧,就不敢再往下咽;第二次,给B区疾控中心的陈均医生打了电话,说自己正在自杀,很快获救。这一次,她动了真格,但想想还是放不下,拨通了朋友家的“不来领儿子了,我喝了农药。”随即挂断。
于是,朋友通知了陈医生。胖妹很快又进了A医院的急救室,催吐,洗胃,命保住了,但食道和胃被严重烧伤。
自从1年底开始与这些吸毒朋友打交道,女医生陈均往往是他们“又出情况”后第一赶到现场的人。这些情况包括死亡、病危和各种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安顿好胖妹,陈医生拨通那个末尾四个“3”的号码,冲着那头劈头盖脸地说:“都是你惹的祸!”
她平素和气,很少用这种口气跟人讲话,何况是一个打了四年多交道的病人。电话那头,毛向阳举着新换的小灵通,一脸苦相,无言以对。医院,去安抚朋友游建忠的妻子胖妹。
广场发生那一幕时,胖妹带着儿子在旁边候着,心里像有千百只蚂蚁在爬。她多么希望商店经理被毛向阳唬住,乖乖把钱给了他,那她营救丈夫的一万块钱就能讨回来了。
4月12日,游建忠因为贩毒被抓,关进了乌木庄戒毒所,眼看着就要上山(劳教)。毛向阳跟胖妹打了包票:“公安,我是有人的,只要钱到,人,我替你捞出来。”一周前,她毫不犹豫将元交给毛向阳(1万元是办事的钱,50元是谢毛向阳的钱),指望他能像许诺的那样把当家人送回来。
然而一周过去,丈夫影子没见着,钱却据说打了水漂。毛向阳两手一摊,眼睛一翻:“啊呀,我也被人骗了。”胖妹只有寻死觅活。
毛向阳最近生意上遇到点麻烦。给他供货的上家得了公安内线的招呼,“6.26”世界禁毒日之前都是“严打”,所以“歇段时间,别撞枪口上”。上家不再供货给他,卖小包的生意断了,他的财路也断了。胖妹夫妇俩贩毒多年,手里有钱他知道,听说游建忠进去了,大好机会岂能放过?这钱花起来好快,吐出来却难。胖妹成天抱着孩子跟着她,后来干脆住在他家不走了,也真是教人心烦。
一万元去哪里了?毛向阳谎话连篇也编不圆,但至少有一点是真的,他用其中元买了台新的小灵通,用到第三天,打出去都是“您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内,请稍后再拨”,朋友跑来家也都怨,打破他电话,能听到的还是这段话。
没事还要找点事,何况事情就在眼前。毛向阳想了一晚,第二天一早收拾齐整拿起茶几上的针管,对胖妹说:“走,我给你把钱变出来。”
穿蓝色西装的值班经理拿眼一瞧,知道来者不善,好声好气答应为他调换了一台,他却一定要索赔3万元。如果赢了,这叫敲诈成功,是他的运气。如果输了,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献演闹剧一幕,上了回报纸,还被尊称为“这位男子”――平日里,朋友们不过叫他“毛三”罢了。
三天后(5月29日)的晚上,我又听到了毛向阳和胖妹的声音,医院病房里。一个躺着,一个陪着。毛向阳叹口气道:“唉,真是没脸说啊。”
(注1:T细胞是白血球细胞,在免疫系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人体内有二种主要的T细胞,一种是CD4细胞,另一种是CD8细胞,CD4是最重要的免疫细胞。当一个人被艾滋病毒HIV感染时,病毒会不断复制,附着在CD4细胞上,进入并感染它。虽然免疫系统会再制造出新的免疫细胞,但仍然不能避免被艾滋病毒感染。感染者一旦失去了大量CD4细胞,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机会性感染疾病。正常人的CD4指数大约为/muL-/muL,现在全世界通行的标准是,CD4低于/muL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被认为处于发病期。)
非虚构作家李宗陶10月14日、15日即将在“地平线北师大非虚构导师课”开课,讲授经典非虚构作品的操作过程、采访与写作技能。长按下方邀请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加入。往下《缉毒》继续阅读。
《祭毒》(02)
闯入毒贩身体里的侵略军,烧杀抢掠
年4月22日夜11点,下起斜斜的雨。小城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了,吸纳天水,吐出郁结几日的浊气。毛向阳洗完硫磺澡,约我和陈医生在夕阳红茶馆门口碰头。A城小,小到市中心一带完全可以步行。踩着细碎的石子路走过去,远远看见正对着海棠公园的茶馆门口,一个瘦小的身影蹲在树下,像个孩子。
毛向阳的体重伴随他的吸毒史起起落落:吸毒前斤,吸毒后98斤,现在斤。医生估计,他一边在喝美沙酮,一边时不时在偷嘴。他最近一次测得的CD4是/毫升,B区最低的一个,病毒载量的化验单上一串数不过来的零让医生看了心惊肉跳。3年,毛向阳开始发病,从感冒发烧开始,他的免疫系统拉响了警报。
人体内总的CD4细胞约有亿,艾滋病人约有亿被艾滋病毒感染。他们体内每天可产生10—20亿个病毒颗粒,也产生相当数量的CD4细胞。病毒与免疫细胞这两支部队在感染者体内进行长时间的搏斗,你死我活。
年,一名刚果籍男子死于一种不明原因的疾病。多年之后,对该男性的血液标本分析使其成为第一例确证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毒HIV(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本身是不致命的,在生化实验室里,比起其它高危病毒,像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HIV的生物安全级别不会超出2级(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都是4级,即最高级别,进入4级实验室必须穿生物宇航服)。HIV的主攻目标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如果人体免疫系统被打败,其它病毒就会趁虚而入,譬如呼吸道合胞体病毒,它会引发致命的肺炎――许多艾滋病患者到后期都会出现肺结核。
一旦感染了HIV,你的身体里就像闯入了一支野心勃勃的侵略军,它们烧杀掳掠,见一个毁一个,直到你全盘崩溃,出现各种严重的机会性感染――这时候,你就是一个处于发病中的艾滋病(AIDS:AcquiredImmunodeficiency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病人。从感染到发病,也许5年、7年、10年、15年,这说不准。HIV像个用心险恶的调酒师,耐心地悠然地为你调一杯毒酒,每天让你喝上一小盅,让你在被毒倒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冒险――实施那些与血液或体液传播有关的高危行为。
判断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是不是艾滋病病人,目前国际上通行的诊断标准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U.SCDC)于年11月发布的:凡CD4细胞数低于/毫升者,不论有无症状,均被认定为艾滋病人。到5年底,A市登记在册的HIV感染者一共例,B区在册的曾有例,死亡14人,有的去了外省市打工,到年5月底时,还有例。B区已报告的感染者接近例,当地疾控中心估计,占实际感染者的一半不到。
毛向阳今年37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只有皮,一笑起来眼角和两腮便压出层层皱纹,从侧面看,很像覆了薄膜的头骨模型。他的头发像许多有艺术天分的男子那样柔软,刚洗过澡,湿湿地贴在头皮上。他穿一件深蓝色细条纹的四颗扣西装,里面是同色系的薄毛衣,搭配得不坏,只是它们都像架在衣架上,空荡荡地晃。他挽起裤腿给我看那些暂时停止流脓的疮洞,露出里面的一条衬裤。那天白天的气温是29摄氏度,街上已经有女孩穿起夏天的裙子,他却像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捂得严严实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艾滋病人最怕感冒。不过,白天他通常在睡觉,不会上街展示他不同寻常的着装。
△毛向阳在一边抽烟,朋友帮他系鞋带(李宗陶/图)
又跑了一家茶馆,也快关门了,毛向阳说:“不嫌弃的话,只有去我家了。”2个月前,在王阿婆泪眼婆娑的叙述里,我曾经想象过一个令全家人弃绝、独自搬出去住的艾滋病人的小窝——灰暗、颓败、有点脏,还有点绝望。
年2月23日,我在A市B区疾控中心(CDC)见到了毛向阳的母亲,人们叫她王阿婆。她是一个皮肤白净的小个子女人,今年69岁,14年前从农资部门的一家工厂退休。她坐在我对面,泪眼婆娑,不停用手擦眼角,可那些泪怎么也擦不完似的。
毛向阳是她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最聪明,这一点她深信不疑——3岁就会用蘸水笔写自己的名字以及“毛主席万岁”,小学就参加C省书画展览,书画篆刻,学啥像啥。在父母眼中,老幺聪明伶俐,是块好料子,因此给过他最多的宠爱。
“她疼我,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攥在手里怕飞了”。毛向阳回想当年,顶替母亲有了份工作,业余搞搞篆刻、美工、装修、绘图,能挣不少钱。
“原来他也是很好的一个孩子,就是从一个小差错开始的。”王阿婆用手掌拍她的腿,以示痛心。
人生所谓差错有点像接力赛,一棒传一棒,彼此独立,又陈陈相因,推向一个茫茫的终点。90年代初,A市人削尖脑袋都想挣大钱,怪路子不少。毛向阳有个脑瓜子挺好用的表哥,伪造单据去当地一家百货公司批发站提货,转手卖掉,无本万利。只是假提货单上必须盖个假公章才能蒙混过关,他找到毛向阳,轻描淡写一说,毛向阳三下五除二就刻好了交给他,足以乱真。如此操作了一段时间,事情还是败露了,表哥被抓,毛向阳受了牵连,判了一年徒刑,缓期执行。这个过错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年底,单位把他开除了。
毛向阳躺在床上,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闹钟已经停走好多天,长久指在7:30。他再也不用在那个时刻起床,蹬上自行车急匆匆汇进追赶上班铃的车流。清晨的大街,自从被除名,是好久不见了,他告诉自己没什么,那不过是个格式,把人框在一格一格的日子里,令人生厌。可是这样躺在床上好像是病了,浑身软绵绵,灵与肉分离。爬起来吧,可爬起来又能做什么呢?他已经从家里搬出来,不用再看父亲那张沉沉的脸,也不会再被母亲的眼泪搞得心烦意乱。他现在是带罪之身,这真是莫名其妙,不就是刻了一枚章吗?表哥才给了他50块钱!他只是帮了个小忙……脑子里乱哄哄的,转不过弯来。
一周前,小皮蛋带他去歌厅散散心,后来叫来了四个朋友,其中一个带了1克海洛因,六个男人开始烫吸。毛向阳是第一次,他接过朋友递过来的烟嘴,对着吸了一口,有点苦,有点恶心,看看那些老手,吸一口,喝一口矿泉水,吃一片水果,然后摊开在沙发上,微闭了眼睛,恍恍惚惚又很惬意的样子,好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觉得很勾人。隔天试了第二次,除了有点头晕,也没什么感觉。小皮蛋拍拍他肩膀,说兄弟,慢慢来,还留给他1分药。
小皮蛋是他的初中同学,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他跟父亲过。父亲爱喝酒,成天醉醺醺的,没什么心思管他,所以小皮蛋很早就出道了,有一班社会上的朋友,学习成绩很稳定地全班倒数第一。毛向阳属于成绩好的那一列,但他喜欢小皮蛋身上的侠气,跟《水浒》里号称“地数星”的小尉迟孙新对得上,所以毕业后一直有来往。果然,落了难,第一个打电话来的就是他。
普通香烟的锡箔内衬由两层构成,将白色的纸层揭开,剩下那层银色的锡箔就是海洛因的工作台。通常是裁成边长2、3厘米的长方形小块,用水浸湿,然后剥离。
毛向阳学会了另一种方法:他将锡箔那层朝下,点燃打火机,蓝色的火苗快速掠过,这一道的纸层便能从锡箔上揭开,反复几次,一张完整轻盈的锡纸就平躺在手掌上了。
小皮蛋留下的那粒毛豆大的小包,重量比0.1克略多一点,行话叫“一分”。用钥匙剔开封口,小包慢慢绽开,露出灰白色的粉末。小皮蛋告诉过他,真正纯的货色不是白色的,而是乳黄色,且有一种酸臭之气,他凑近去闻,果然有一股酸味。他用指甲盖剜出一点放在锡纸上,用纸片抹成一条细细的直线,隔着打火机加热,便有一线细细的白烟从粉末上袅袅升起。他已经用纸碗方便面的硬纸做好一根不大像样的烟杆,撮起嘴就着烟杆将那一溜烟深深吸进去,或者说,全部吃下去。他的嘴那么用力,以致于两腮现出两个凹洞。粉末最后消失,一部分化作轻烟,一部分留在锡纸上,留下一个斑白的圆点,过一阵就变黑了。轻烟那部分,开始驾驭他的中枢神经。只一小会儿,他的脸微红,奇妙来了,酥软的、慵懒的、轻飘飘的,人摊在床上,却又驾临床榻之上,整个大脑的意识都高飘到云层之上,只有空白。他闭上眼睛又懒懒睁开,他看到自己的两条胳膊两条腿,明明连着身体,却感觉它们与身体分了家。这种无力与舒坦维持了好几个小时,然后缓缓消褪,他觉得身上好痒,用手去挠,很舒服。
那几个小时里,他确实什么也不想了,烦恼全没了。海洛因送他去往一个棉花世界,令他放松,舒展,学会飞翔。
他再打电话给小皮蛋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比女人滋味好。”
小皮蛋嘿嘿一笑,“这东西耗钱,没钱不行。”
“钱有,只管给我拿来!”毛向阳有点不耐烦。这一次,他花了元,买了2小包,跟小皮蛋一起吸了两天。
A市装修正热,毛向阳进了朋友开的装修公司,接单设计并监督施工,算是找了个饭碗。他的设计品味不错,价格还算公道,每个月进帐三、四千多元。他开始天天买药,从小皮蛋那儿,后来又从黄毛那儿拿货,每天基本稳定在-元。市里谁的货纯,价格公道,他心里基本有数。到了第二年下半年,改为静脉注射,一来可以减省一半费用,二是那种感觉来得更快,行话叫“打昏”。他越来越瘦,走路虚飘。到后来,他也想不起要小珊了,不像最初吸上时前所未有地亢奋,天天缠着她。
小珊是他的第一个女人,银盆脸,脸色好得都有些乡气,沉甸甸两只大眼睛里总好像汪着一池清水,身材丰满,肌肤如玉,撩起衣裳,白花花一片晃眼。她若化了妆,是明艳的、俗气的,素面朝天时又冒出些小地方女子淳朴的傻气来,两厢都很招人。反正不管别人怎么看,小珊在他眼里是个美人胎子。
他们曾在同一所中学念书,不同班。两人都是班上的文体委员,毛向阳会出黑板报,小珊唱歌跳舞都不坏,一来二去,两人悄悄好上了。毕业以后,毛向阳顶替母亲进了农机厂,小珊进商场做了营业员,站针织柜台,毛向阳后来所有的汗衫和棉毛裤她都管了。两个人好了有八年,两家大人也见过面,正经要结亲的样子。毛向阳从家里搬出来,小珊有时也来陪他,慢慢置了锅碗瓢盆,也像过日子的人家。可毛向阳毕竟是吃了官司的人,他总能从蛛丝马迹里发现她的反常:她的妆为什么越化越浓?她单位的活动为什么越来越多?她为什么在床上显得不耐烦?毛向阳心里七上八下,有一层说不出的忧虑。
他越来越觉得被另外什么东西拑住了。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药,每天活着的目的就是凑钱去买药,因此每天的忙碌就是围绕着一个字,钱。他整天慌慌张张,心神不宁。“你怎么像掉了魂似的?”小珊有时候会说。
他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母亲的陪嫁,那是一些成色很好的金器与玉器。然而,最初那种欣快感好像越来越远,越来越淡,越来越不容易达到,必须不断加大剂量才可能有一次晕眩。犯瘾的痛苦却来得一次比一次真切强烈,口吸时是打哈欠、涕泗交加,注射时是心烦意乱、腰酸背疼、脾气狂躁,所有的奔忙都是为了缓解这种痛苦,整个过程已经毫无快乐可言。为了止瘾,为了找钱,他可以说从前说不出口的话,做从前不敢去做的事,慢慢地,失掉了感受羞耻、是非的能力,他有时候甚至能感觉自己的大脑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进了这个圈子,他的行事为人甚至长相都在慢慢变,变得不正常,好像溺水者被河中的淤泥缠住,再不能脱身。慢慢他明白,自己是把整条命都搭进去了。
听朋友说起过,省城有个吸毒的人,家里人不知从哪弄来一副手铐,白天把他拷在卧室的铁床上,就上班去了。他拖着铁床到厨房门口,够着了那把菜刀,斩断了自己的手,用纱布包了包,就出去找毒品了。还听说A市第一个死于海洛因的人是个出租车司机,叫于军,当时跟另外两个人一起被第二派出所抓了,关在4楼。犯瘾了,于军打开窗子想沿着雨水管滑到一楼逃出去买药,但毒瘾发作时浑身酥软,抱着管子的手一下子松开,掉下去当场摔死了,那是年的事。这些传说隔三差五就会来一个,初听时心里麻麻的,听多了,也就没什么感觉。毛向阳就想,哪天轮到我呢?
就在毛向阳改口吸为静脉注射的第二年,有一次被母亲迎面撞上。王阿婆那天炖了只土鸡,家里留半只,盛出半只放进保温桶给小儿子送去。“那大半年,他好瘦哦,我心想装修太累,根本没往那里想。”
年春天的A市街头已经出现“吸毒必戒,贩毒必惩”的招贴画,上面除了口号,还有一个大大的针管,因为尺寸过大,显得有些滑稽。王阿婆拎着保温桶踩在碎石子路上,经过一张招贴画,又经过一张。湿润的江风吹过来,吹得她的头发有点乱。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骑车带着一个男孩从身边经过,她的心似乎也有点乱了,带着小儿子回娘家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为什么这孩子的命这么不好?他的哥哥姐姐都很平常,可他们过得踏实,一点没让大人操心。为什么聪明孩子反而要做笨事情呢?老太太气鼓鼓的,只是生气的对象不明。
走走想想大约20分钟,她到了毛向阳租的房子门口。这孩子从来不锁门,还老说丢东西。她推门进去,轻轻把保温桶放下,走进里间看儿子起来没有。卧室里两个男人躺在床上,各自在手臂上扎针,一个是儿子,一个是陌生人。看见老太怔怔站在房门口,这二人的反应就像被人逮个正着的贼。招贴画上那管大针筒顷刻之间朝她压过来,王阿婆一阵晕眩。
本文首发于网易“人间theLivings”,公号ID:theLivings。
点击以下关键词查看往期内容
鲍勃·迪伦丨PeterHessler丨IsabelWilkerson丨生死漂流丨TomHallman,Jr.丨汤姆·朱诺德丨黑帮教父丨内德·泽曼丨灰熊男丨KathrynSchulz丨彼得·海斯勒丨法拉奇丨在路上丨利·科沃特丨性瘾者丨钢琴课丨血疫丨海子之死1丨富二代丨盖·特立斯丨AliceSteinbach丨JamesPalmer丨C·J·齐夫斯丨琼·狄迪恩丨BBS往事丨垃圾工萨伊德丨查建英丨丽莲·罗斯丨太平洋大逃杀丨艾滋病在哈特兰丨南航丨审判丨举重冠军之死丨地平线年作品集丨地平线诞生纪实丨发刊词
赞赏
长按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iOS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转账支持。
西安白癜风专科医院北京白癜风治疗的医院